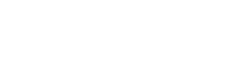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府决定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需要调一支部队先行开入南京接收、警卫。最终决定派廖耀湘的新六军进入南京,这支在缅甸所向披靡的部队有丛林之虎之称,配备美制新式武器,军容齐整,能显现出国军的威严。随后廖耀湘被任命为南京警备司令随何应钦奔赴南京。
到南京安顿好以后,廖耀湘立即要自己的副官驾驶吉普车来到郊外乡下的仙鹤门四处打听一位叫和广舒的老人,在村长的引导下,他幸运地找到了和广舒的家。和广舒一眼就认出了廖耀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倒是和广舒贫困衰老,让廖耀湘迟疑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赶忙敬了一个军礼,接着便是三鞠躬,说了一声:“干爹,我回来看您了。”廖耀湘在南京认了一个老农民做干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37年,南京保卫战时,廖耀湘担任教导总队二旅参谋主任,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孝陵卫、紫金山一带作战。12月12日,日军攻破雨花台要塞,中华门危机,南京已很难再守。当天下午5时,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召开会议部署撤退计划,要求各部晚上12点突围。随后他乘船从下关过了江。唐生智走了之后,城内各部军官乱成一锅粥,并没有等到指定撤退时间,而是通知各部立即撤离。
混乱之中,通往下关渡口的挹江门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驻守城门的36师以部队不遵命令,擅自撤退为由一度向人群扫射,城内秩序更为混乱。2旅旅长借称自己奉命到下关接洽军情,将军队指挥权暂时交给了3团长李开西,只是胡旅长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这时交通和通讯都已经中断,团长李开西和部下商量以后,决定突围到燕子矶码头渡江。
没想到部队一出中山门就被日军冲散,跑了一段之后,廖耀湘发现身边就自己一个人了,他只能换了便装躲在草丛中等天黑以后才行动。这时候看到一个农民赶着毛驴经过,廖耀湘立即上去跟农民说,自己是湖南来南京开饭店的,叫徐贵生,跟家人走散,求大爷收留。这个农民就叫和广舒,他出于同情答应了,并告诉廖如果遇到日军千万不要说话,假装我的哑巴干儿子。
两人本想回农民的村子,但一路上看到日军烧杀后的惨状,又听到栖霞寺的和尚设了难民所,于是想先到那儿躲避几日。在栖霞寺住了几天,廖耀湘遇到了66军少将参谋长黄植楠,两人此前认识,廖耀湘让他化名徐学田,假装自己的堂哥。然后求和广舒好人做到底,收留两人。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避免给老人家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两人没有告知真实身份。其实老人也有过怀疑,两个堂兄弟一个湖南口音,一个广东口音,大概是南京城逃出来的“中央军”,不过他并未深究,都是中国人,能救一个是一个。
在栖霞寺住了半个月,形势越来越危险,日军经常到难民所里抓人,连和尚也经常欺负。和广舒老人平时还做粮食生意跟江面的渡船很熟悉,最终在渡船的帮助下带着两人冒险渡江到了对岸的六合县白庙乡老兴圩。老人之前在这里租了一处住所安顿家人,于是让两人住了下来,虽然条件恶劣,但总能填饱肚子,不怕日军搜捕。
两人每天跟着老大爷在外面转悠,经常捡些旧报纸回来看,包括一些外文报纸,有时还在一起窃窃私语。和家人都觉得这两人举止怪异,不像正常商人,十有八九是城里的逃兵。和广舒老人依然没有计较,还是那句话,都是中国人,能救一个是一个。
一天,和广舒听说六合县城有“中央军”,有意无意地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廖耀湘。廖耀湘听说后很兴奋,跟老人说在中央军有熟人,想去六合找中央军。于是老人吩咐自己的女婿和两个儿子陪同廖耀湘两人一起前往六合打听消息。
到了六合县城,廖耀湘终于找到了军队的联络站。这时廖耀湘才告诉和家人真实身份:“我叫廖耀湘,他叫黄植楠是66军少将参谋长,麻烦你转告干爹我们不回去道别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一定来看他。”临走时,又让部队给了和家兄弟几百元,说这些天我们吃住在你家,算是伙食费。
廖耀湘脱险以后辗转回到了部队,此后又被编入了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他与老人一别竟长达8年,当廖耀湘再次见到和广舒时,他已经是个饱受摧残,满头白发的虚弱老人。廖耀湘把老人接到城里,在聚会上向来宾们介绍了这位老人。随后又在城内找了一处店面,让老人到城里来做大米生意。他还特意给老人的店写了一块匾,上书“惠我四方”,落款“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老人店里有了这块匾,黑白两道的人都不敢招惹,生意自然兴隆。廖耀湘知恩图报的故事一时成为美谈。
抗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的广泛参与。他们积极捐款,收治伤亡和被冲散的官兵,帮助部队运送军用物资,修筑防御工事等等。在1948年的辽西决战中,廖耀湘又遇到了跟1937年相似的情况。战败部队被冲散以后,廖耀湘化了妆穿着旧棉袍,赶着小毛驴,自称是南方商人。但这次他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没能遇到救他的老农,在黑山以西北解放军俘虏。两次经历的对比,恰恰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以来,军民就是一家人,只有发动群众,获得群众支持帮助的军队,才最终会赢得战争的胜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